
识别二维码或者扫码
关注公众号

识别二维码或者扫码
关注公众号
前几天,久未露面的李宇春上热搜了,但不是什么好事:
她病了。
强直性脊柱炎。
严重的时候,脊柱痛到要坐轮椅。
用她的话说,是一种“石化”了的感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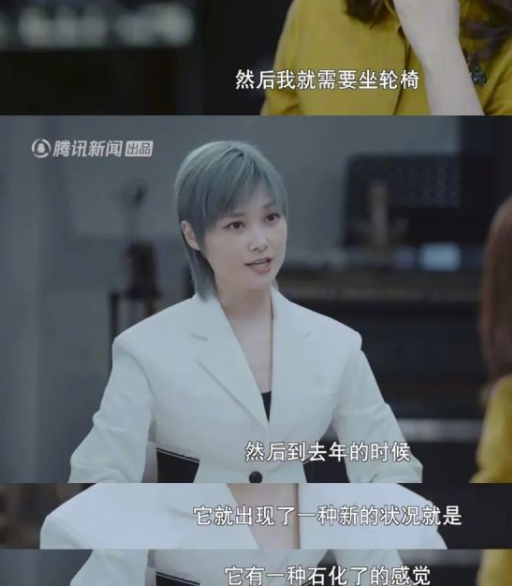
这种病,周杰伦有,张嘉译有,不管谁摊上了,都意味着终生的“缠斗”。
强直性脊柱炎号称“不死的癌症”,是一种免疫性疾病,也就是俗称的“风湿病”,通常要去看风湿免疫科。
这个病是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,错误攻击自体组织,在骨关节的位置产生炎症,导致软组织纤维钙化,时间一长,最后发展为全脊柱纤维化和骨性强直,脊柱或四肢的大关节就像生锈了一样,不断硬化,动弹不得。
轻的就像张嘉译,走路总是驼着背,摆来摆去。
重的就像这样,头都弯到了大腿上,一辈子只能盯着地面。

安徽有个读医7年的年轻人,不堪疼痛折磨,毕业后几年就自杀了。
38岁的李宇春算是幸运的,她的病还没到最严重的阶段就被确诊,可以持续规范治疗,延缓病情进展。
有一个“四字弟弟”,也是30多岁,身体已经弯成了一个“C”字,做了3次大手术,身体被“砍”断3次……
▽
从“四字弟弟”到“C字弟弟”
“30多岁了,最远就去过镇上”
“四字弟弟”原本叫董长生,小时候家里算命,说他命中缺水,就把名字改成了四个字:
董长水生。
水有了,命却没变好。
从13岁开始,水生的身体就感到疼痛,17岁出现腰痛,因为弯腰时可以缓解,不知不觉后背就越来越驼,久而久之脊柱严重弯曲。
32岁时,“四字弟弟”成了“C字弟弟”,头也抬不起来,脸快贴到肚子上。
他能看到的世界,几乎只剩地上的两三米。
疼痛发作时,他走路要撑着一张矮凳,一步一步挪,凳脚越磨越短,凳子已经换了四五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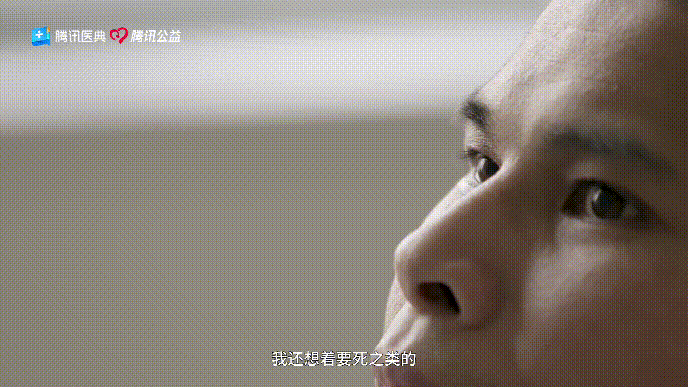
他每天躲在家里,畸形更严重前,还能洗洗衣服、切菜做饭,唯一称得上“工作”的,是坐三轮车陪妈妈去三十公里外的镇上,收些米糠回来喂猪。
镇上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了。
每次坐车,他的眼睛都不敢往外看,周围的人“一直看着我,看很久”,他只能把头埋得更低。
水生家在广东韶关的农村,他去过几次医院,医生都说“没办法治”。
钱花了七八万,那是家里的大部分积蓄。
父亲骂他,得这样的怪病,都怪你老是在家里呆着,不出去锻炼。
母亲护着他,小到拿个指甲钳,大到洗澡,都随传随到。
但母亲帮不了他的痛。发作严重时,坐着、站着、躺着,痛感一刻不停,止痛药也没用,水生动弹不得,除了哭,没有任何办法。

第一次知道“强直性脊柱炎”这个词,是水生有了手机后上网搜到的。
他读了几篇科普文章,内心毫无波澜,毕竟这么多年了,早就不抱希望了。
有一天,弟弟拿着手机跑过来,给他看一个视频:
你看这个人,身体都折叠起来了,还能掰直。

视频里的病人叫李华,被医生称为“3-on”折叠人(on可理解为贴着)——
脸贴着大腿
下巴贴着胸口
胸骨贴着大腿骨

经过四次“粉身碎骨”的手术,李华的身体竟然像折刀那样打开了,他又重新站直了。
水生无法从脑子里移走这些画面,他决定,赌一把。
两兄弟决定一起去深圳,找这个主刀医生做手术,但父亲不相信手术会成功,母亲觉得这是赌博,担心钱花了,最后人还瘫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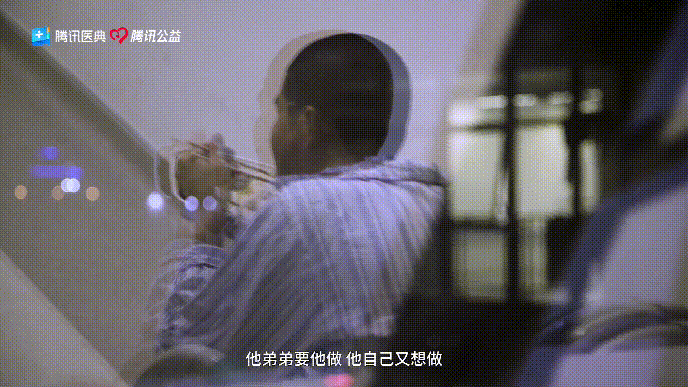
卖了1头猪、2只猪仔
两兄弟来到了深圳
出发前一个星期,水生家里卖掉了一头猪、两头猪仔,加上亲戚给的,凑了一万多元。
在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的病房里,他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多看起来和自己一样的人。
比如来自河南周口的李润顺,平日除了蹲在地里帮家里分担农活,从不出门,“闲言碎语太多了”。
几个人一起弓着背在走廊里,就像白雪公主身边的小矮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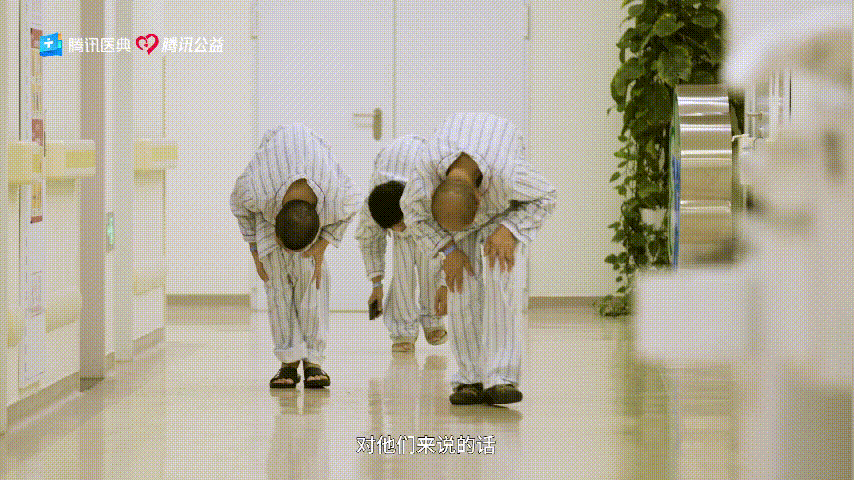
在第一次手术前,护士问水生最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什么。
“瘫在床上。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在那个床上躺着,一动不动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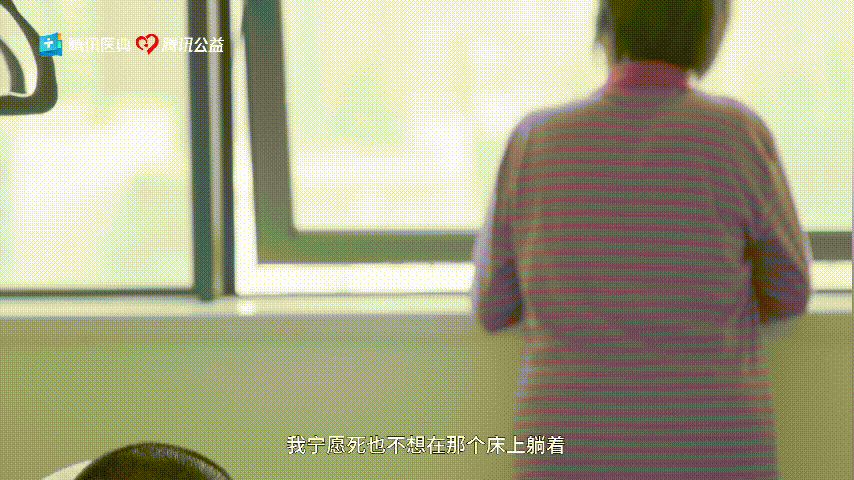
将要为他们主刀手术的,是深圳大学总医院的副院长、脊柱骨病科主任陶惠人,也就是李华的主刀医生。
陶惠人说:“如果把治疗李华的难度比喻成珠穆朗玛第一高峰,那董长水生就是第二高峰。”
脊柱畸形手术被比喻为骨科里的皇冠手术,“手术难度和风险特别大,稍有不慎,不是死就是瘫。”
术前,医院召集了多个科室进行多学科会诊:麻醉科、放射科、呼吸内科、消化内科、护理部、感染控制科……

最后敲定了一个“三部曲”的手术方案。
把身体打断3次
重新接起来
手术“三部曲”
第一场手术,“打断”胸椎:
病人侧身卧着,进行胸腰椎截骨,让上身张开约80度;
第二场手术,“打断”大腿:
置换掉双侧大腿根部的髋关节,将腿和身体的距离打开,同时让大腿能转动起来;
第三场手术,“打断”腰椎:
病人趴着,进行腰骶椎截骨,将身体再打开约40度。
第一场手术,麻醉是关键的第一步,病人身体像水果刀一样折了起来,气管插管时,怎么把管子插进喉咙去?麻醉科主任孙焱芫又成了手术室里嗓门最大那个人,指挥着整个麻醉团队摆位、配合……

这场手术历时8个小时,水生的身体被成功打开了80度左右。
从手术室被推回病床后,水生慢慢恢复意识,手在床上虚弱地摸索,“碰不到膝盖了。”
一旁的护士问:“你是发现身体到膝盖的距离变大了,开心是吧……你看他,笑了。”病房里充满大家爽朗的笑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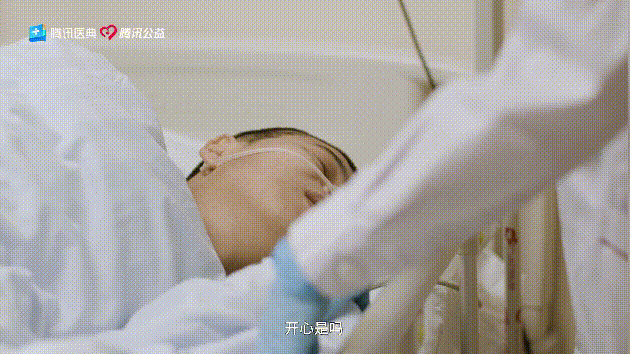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场双侧髋关节置换,陶惠人请了老同事吴尧平从西安打“飞的”过来主刀,他是国内著名的关节外科专家、西京医院骨科教授。吴尧平切开髋关节的皮肤一看:“他都没有像样的骨体了,像空壳一样。”
这是得病后长期缺乏活动和锻炼导致的重度骨质疏松。

吴尧平医生在给水生做手术
吴尧平要在关节置换处安放臼杯,小了容易脱位,大了关节的活动度就不好,如何平衡,全靠几十年经验的精准拿捏。
几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,吴尧平正要走出手术间,忽然转过身来,挥起右手的拳头,对着还未醒过来的水生连喊两声:“不要脱位!不要脱位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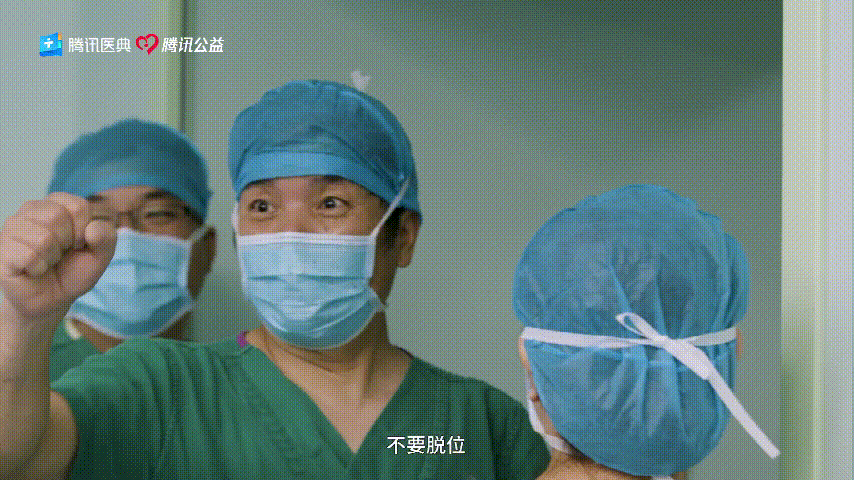
水生迷糊中醒来,第一句就问:“吴教授有没有走?让我见一下他。”
第三次“打断”腰椎的手术,对于主刀医生陶惠人来说是最困难的。水生太瘦了,皮肤很薄,趴在病床上进行腰骶椎截骨时,他的背部被划开一个口子,随着矫正器械的撬动,水生的腰骶椎发出一声清脆的响,“啪”!那是骨头断开的声音。
把水生的身体拉直时,好几个医生钻进无菌手术单下,跪在手术床旁,分别扶着水生身体的上下部,跟着陶惠人的口令,缓慢地将它们分开。反复抬了好几次,坚持了几十分钟,才将断开的脊柱扶成一条线。跪了许久的医生们,脚都麻到站不起来了。
三场手术,五个月,水生终于直立站起来了。
每天早上七点多,他扶着助行器在病房里走两圈,再到走廊里走两圈。那些对正常人再熟悉不过的走路的动作,对他来说就像个小婴儿学步,笨拙得很。僵硬的手臂也还没恢复灵活,连衣服都很难穿上去。

水生在病房内锻炼
晚上躺平时,背上的切口压得生疼,但让水生感到高兴的是,那些来来去去关心他的声音终于能对上号了,看得见是谁的脸了。

“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”
术后一年再来深圳复查,水生去了趟深圳湾,一步一步缓慢走进公园,跨过一块块粗粝的大石头,站立在候鸟飞舞的岸边,海风夹着腥味扑面而来。
命里缺水的他,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大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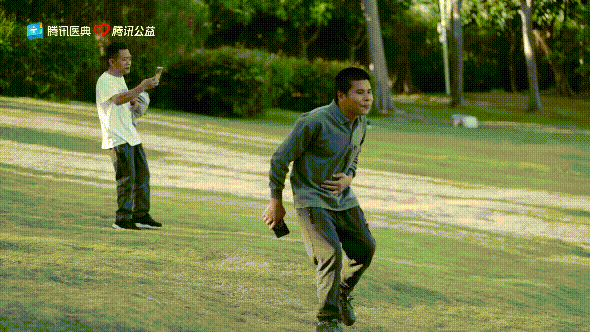
他终于改命了,但并不是因为名字加了个“水”,而是遇到了“贵人”——陶惠人。
陶惠人曾是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“老军医”,2019年从西安来到深圳,他做过近万台各类脊柱手术,救过侧弯超过100度的严重脊柱畸形病人,是全国治疗脊柱畸形例数最多、效果最好的医生之一。

但当李华、董长水生、李润顺这些病人出现在他的诊室时,他还是叹了口气:这或许是脊柱外科领域最困难的病例了,没有先例。
他们本不该来到这里。
强直性脊柱炎虽然号称“不死的癌症”,但其实是一个慢性病。
“这个病只要早发现、早治疗,一般都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。往往都是发现得晚了,没有及时去治疗,耽误成这样。”
陶惠人相信,随着医疗体系的进步和医学科普的传播,“也许再过二十年,我的学生们就再也遇不到这么严重的病例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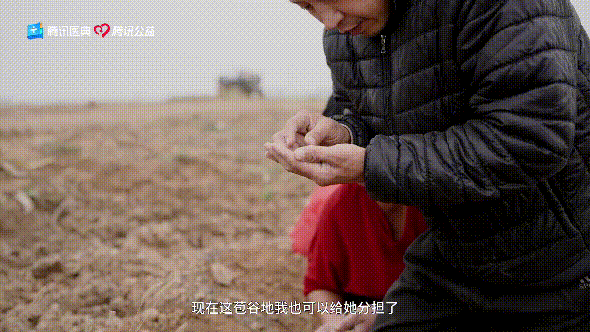
-End-
「有用就点在看」
本期封面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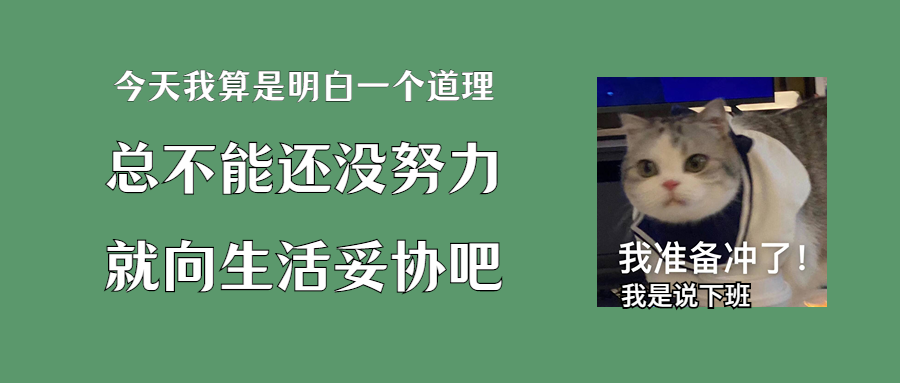
信息来源:深圳大学总医院、腾讯医典

焦睿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
肖丹 广东省人民医院